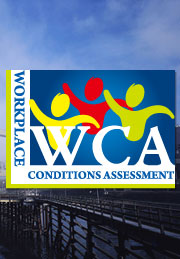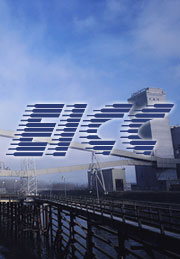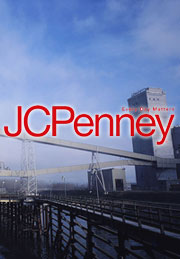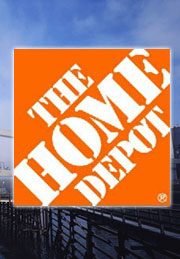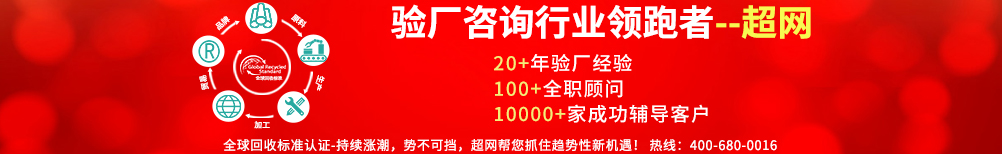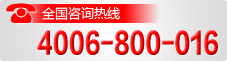電話:18605772928
地址:溫州平陽縣鰲江鎮金鰲路21幢
3單元201室
電話:021-51029391
手機: 18601606208
熱線:4006-800-016
郵箱:chaowang@tranwin.org
地址:昆山市花橋商銀路1255號雙聯國際商務中心6幢4樓(郵寄)
名牌霸權下的勞工與消費者
要飲汽水,你會立刻想到可口可樂、百事;要買運動鞋,你會想到Nike、Reebok、Adidas;要買化妝品,你會想到資生堂、倩碧、蘭金。 呸!這有甚么新鮮?──有人說。
不,是有新鮮的地方的。誠然,廣告之作為商品的「靈魂」,自從資本主義發展以來,已經有許多年歷史了。不過,在廿世紀的最后廿年,的確有了新發展。越來越多大企業發展為跨國公司;而且越來越多企業不再自行生產商品,而是把錢主要花在推廣品牌上(包括重金禮聘超級球星或名人來促銷產品)。這是因為,媒體越是多元,就越能使名牌深入人心;越深入人心,則產品越有銷路。他們認為,經營品牌比經營生產更重要。「機器會折舊,汽車會生銹,只有品牌永存。」難怪全美的品牌每年花費2000億美元推廣其品牌。
結果,名牌這種無形資產的市場價值往往比一間企業的所有有形資產的價值還要高。1988年Philip Morris用126億美元收購卡夫Kraft是一個有名例子,因為卡夫的有形資產只占收購價六分一;六分五的價值屬于名牌的價值。Nike從1987到1993年,六年間從7.5億美元資產的公司發展為40億美元的公司,靠的就是花巨資在制造名牌效應。「想做就去做!」(Just Do It!)成為Nike在新時代的呼聲。事實上,廣告行業不再是推銷「產品」;它們推銷的是「生活方式」;它們就是另一種夢工場。所以Nike不只是賣鞋,而是出售「自由自在」的概念;寶麗來照相機的老板說:寶麗來不是一部照相機,而是促進社交和諧之物;Swatch說自己的產品不只是鐘表,而是一種「時間概念」……
不過,這種蠻后現代主義的漂亮廣告的背后,還是依靠無數非常現代的血汗工廠在幕后運轉。名牌越來越令人飄飄然,但制造產品的工作卻越來越沉重。 Nike發源于美國。但是美國總部的九千員工中沒有一個從事生產,而是從事管理、技術開發、物流及推銷。曾經一度生產鞋子的美國工人,早就全被裁員了。通過分判制度,Nike把生產通通外判到南韓、臺灣,以及泰國、印度尼西亞及中國。全球共有七萬五千員工以極低微人工為Nike造鞋,但沒一個是Nike的雇員,Nike亦對他們不負任何直接責任。這就是所謂「全球工廠」。越多美國消費者買了Nike的「想做就去做」的自由概念,全球七萬五千員工就越沒有自由,越要賣命干活。而原先生產鞋子的美國工人,則享有另一種自由 ------ 失業的自由。這就是品牌霸權的新時代。
-品牌與分判制度-
在這個新時代,品牌的實際生產早就從發達國外判到工資低廉、勞保不完備的落后國。在亞洲,早期的分判制造商是南韓、香港及臺灣,后來推廣至泰國、中國、印度尼西亞、越南等。最近則已擴展至柬浦寨及緬甸了。今天,原來的韓港臺商大多變成第一層的分判商──他們承接了品牌的訂單,把本國的廠房關掉,然后把機器搬到其它落后國開廠,聘用當地的廉價農民工繼續為品牌生產。但實際上,有很多品牌并非全由第一層的分判商生產,而是由前者把工序再分判到第二、第三以至第四層的分判商去生產。這種層剝式的分判制度普遍存在,據說迪斯尼在全球就有15,000個供貨商,而美泰玩具單在南中國就有350家分判商。
工序最后判到工資最低、勞動條件最惡劣的情況下進行(全球零售業一哥Wal Mart已在緬甸進行生產)。最底層的分判往往把工序再分判到最不受法律保障的一群----外發工(Homeworker),她們大多拿不到當地的最低工資,更享受不到任何勞動保護。
-落后國逐步擠身工業國?-
有不少人會以韓港臺為例,認為這些替跨國企業生產的落后國,終有一天會像當年四小龍般經濟起飛,逐步上升為發達國。最近龍永圖就說過類似的言論。究竟今天的落后國擠身發達國的機會有多大呢?答案其實很簡單。
當世界上只有少數幾個國家或地區為品牌生產時,他們成功的機會自然較高,韓港臺正是這樣被跨國企業選中而成功的。但當世界上每個落后國都爭相開發出口加工區,以至割喉式地競投跨國企業的合約,結果就不一樣了。現在全球有70個國家設立了超過850個出口加工區,它們爭相以極優厚條件吸引外資投資(當中包括以禁止工人在加工區內罷工及組織工會作招徠)。跨國企業自然樂于見到競爭,這使它可以選擇出價最低的分判商,同時更可威脅隨時會把生產分判到工資更低的地區。
落后國之間的惡性競爭結果自然導致當地工人工資太低,花不起錢買較好的消費品,甚至普遍缺乏消費力。但更甚的是當地分判商所得的加工費極微薄,根本很難積累大量資本而達致經濟起飛。
舉一個例,美國玩具品牌美泰(Mattel)的芭比娃娃超過一半在中國制造,零售價是10美元,其中有8美元是用在美國境內的運輸、市場零售、批發以及利潤,而余下的2美元中,香港占了1美元管理運輸費,臺灣、日本、美國及沙特阿拉伯分占65美仙的原料費,剩下的35美仙是勞動力價格(包括提供廠房、勞力和電力)才由中國獲得。
再者,大部份跨國企業都跟Nike一樣,只把生產工序分判外國,卻把研究及技術開發(R&D)的高增值部份留在本國,據說是為了防止概念被抄襲。但有人說分判商的工廠根本談不上是工廠,那不過是「勞動力倉庫」,因為工人只是生產在線的裝配工,不算在制造甚么。這顯示落后國家能從中獲得的技術知識相當有限,也說明發達國只想利用落后國的廉價勞工為其賺取超額利潤,而R&D則牢牢握著不轉讓。試問這種「國際分工」又怎會使現時的落后國擠身先進工業國之列呢?可見,分判制度會令落后國像亞洲四小龍那樣逐步上升為發達國的經驗,不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
-工人與消費者運動-
上面提到,生產國的工人工資低,根本買不起自己制造出來的名牌產品,所以這些產品大都運到有消費能力的發達國去銷售。但其實發達國也有許多消費者買不起這些名牌產品,因為產品雖在落后國以前所未有的低成本生產,但每件產品在發達國的零售價往往沒減,甚至可能比過去更高。即是說品牌跨國企業是靠兩邊剝削----既剝削勞工,也剝削消費者----來賺取超額利潤。
所以,如果要有效打擊品牌跨國企業,消費者運動必須與當地的勞工運動緊密合作,互相支持才較容易有成效。例如去年泰國Master Toy玩具廠因港商搬遷而引起工潮,香港玩具生產安全約章聯席發起聲援,最后二者的共同努力使其品牌聲譽受損而獲勝。